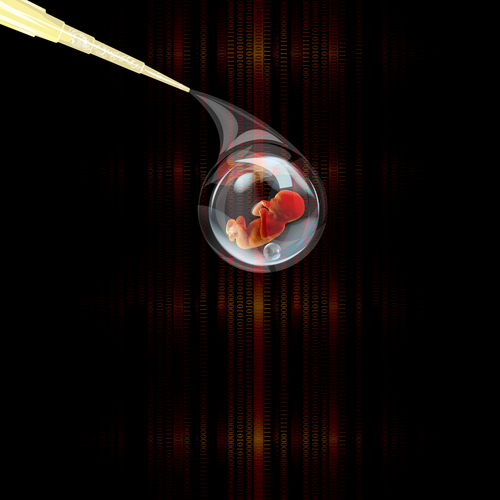 如果说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了水,那么基因就构成了我们的存在。不过,基因能够决定一切吗?Shutterstock 友情供图
如果说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了水,那么基因就构成了我们的存在。不过,基因能够决定一切吗?Shutterstock 友情供图
(文/Kenneth Weiss,Anne Buchanan)DNA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象征,它传达了一个有力的概念,即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可以归结为一串明确的决定性代码。到哪里都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宾利汽车公司称赞自己的员工说:“勤奋刻在我们的DNA里。”足球明星贝克汉姆说:“足球写在英格兰的DNA里。”旧金山金门大桥的收费员说:“我们的DNA就蕴含在这座大桥中。”
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话并不能当真,但我们能明白其中的寓意。这些话不光反映我们所思,亦影响我们所想。就连生物学家也难免犯错,常常把基因所不能之事硬套在它们头上。DNA之所以成为一种象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深信基因是一种一清二楚的东西,它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从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固定了,并且可以被预测出来。如果说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了水,那么基因就构成了我们的存在。
我们被这样的说法团团包围。每周的新闻故事都宣称找到了决定这样或那样性状的基因。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基因测试和血统测定市场欣欣向荣,因为顾客相信他们的基因中所蕴含的东西,比他们的先辈或者家庭故事中的更多。顾客们也想知道他们是否注定要遭受某种疾病的困扰,他们认为这些就写在他们的基因中。精子银行建议准父母要考虑捐献者的习惯、语言、喜好的食物和受教育程度,仿佛这些都写在捐献者的精子中一样。
基因于我们,到底是什么?
但事实并不像想的那样,看看现实世界就会发现,并不是我们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还原为基因。确实,把人身上种种的因果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基因作用的想法,在很多方面已经跟不上时代。即使是没什么生物知识的人,也知道基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一些复杂的性状,例如人都会患的疾病,就是多个基因相互作用或与环境互作的结果。要预测疾病,不但是要检测基因型(就是所遗传到的特定的DNA序列),还要预测未来的环境(吃什么、喝什么、呼吸什么、服什么药物,等等)。这一点无论是测序公司还是“专家”都做不到。
因为环境变化多端,而基因组又独一无二,对某个特定的遗传性状或疾病的几个实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测序公司所估计的疾病风险只是遗传概率,而非确定结果。对于基于行为学性状来选择精子捐献者也是同样道理——任何遗传因素都有可能在捐献者的饮食或者能否上得起大学这样的文化或环境因素面前显得无力。
公司和民族都有自己DNA,这种说法以及DNA具有明确的决定性作用的信念,或许能使人更易于理解这种比喻所要表达的因果关系。不过,这就如同用现代科学上“基因”的概念,来替代宗教上“灵魂”的概念,是颇具误导性的。这种方式倾向于赋予其一种固有的形而上的本质,如同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译者注:一种天主教学说,主张人类不能通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这把原本复杂的现象过于简单化了(如同教条式的信仰)。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样的结果。

既然基因是生命最基本的决定性元素,似乎只要对基因了解得够多,我们就能预测关于自己的每一件事,包括健康、行为,还有思想。但其实这是做不到的,至少现在还不能。Shutterstock 友情供图。
基因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基因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自身的重要信息。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基于你的基因型,你有15%的可能性罹患心脏病。这是一种风险、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必然。可能性并不等于“原因”,两者的意思完全不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抛硬币决定谁买单的时候,可以说拇指是硬币抛起来的原因,但我们关心的是实际的结果,即是正还是反的可能性。
但可能性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抛一次硬币,正反的可能性是五五开,这不难理解。但要抛多次硬币呢?通过一个人的基因型预测未来的疾病风险,就如同预测抛多次硬币的结果一样。每个人都有数百个包含着与疾病发病率有关的独特变异的基因,每一个变异起什么作用,也像抛硬币一样决定“疾病”或是“健康”?——这真的是个问题吗?
预测疾病不像是抛硬币,仅仅只有正反那么简单(如果硬币重量匀称,那么正反两面的概率相同);疾病预测是通过已知的信息,推断或猜测与每个人的基因变异相关的疾病风险,每个基因所代表的患病风险不同。当谈到基于从一个人的基因中所能预测的内容做出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可能性又有几何?就算是一枚正面概率偏大严重的硬币,也还是有可能抛出反面。一个人可能带有糖尿病的遗传风险,但并不会真的发病。并且就算是疾病的风险决定无疑,人的感知也很容易将风险夸大。如果某个疾病在人群中的风险有2%,就算根据你的基因型,患病概率大到25%,其实你患病的实际概率也只是变成了2.5%。
到此,我们考虑的都是基因对纯粹的生理性状的影响。那么,基因对行为乃至意识和自由意志等终极问题这般的非生理性状,影响又如何呢?“基因”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取代了“灵魂”的象征地位。我们的感受、思维和行为到底有多少是在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就决定了的,这些东西能像电脑程序一样从我们的基因组中读取出来吗?
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由意志,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对很多宗教而言,这同我们能否为自己的德行负责有关。科学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物质、能量和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作用力所构成的世界。既然基因是生命最基本的决定性元素,似乎只要对基因了解得够多,我们就能预测关于自己的每一件事,包括健康、行为,还有思想。而“灵魂”则有神秘主义意味,认为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能够影响我们是谁、做了什么事情。不过,如果基因预测如此的复杂且不可靠,为何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受基因宿命论束缚这么严重?要是基因不但能用以解释生理性状,也能说明像自由意志这样的抽象性状呢?
基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
基因当今的象征意义,是由从19世纪起的两条主线编织而成。1858年,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了令人咋舌的新体系来理解生命,这一体系完全是唯物的,脱离了神秘主义的桎梏。他们称,生物的多样性是源于共同祖先的趋异演化,生物现在的性状与功能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学说产生在一个信仰牛顿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科学是依照“自然法则”来了解存在。达尔文在其演化生物学的奠基之作《物种起源》中表示,在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中,自然选择同重力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基本的决定性力量。
演化决定论是基因比喻的第一根主线——自然选择只保留遗传来自过去的成功生物体的性状。另一根主线则来自一位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人,格里哥·孟德尔(Gregor Mendel),他通过研究豌豆了解遗传的本质。孟德尔的发现也完美切合了牛顿式的世界观。如果说自然选择像重力一样,是自然法则,那么孟德尔遗传定律便为探明构成生命的基本组件带来了希望。孟德尔通过选择特定的纯合形状发现了遗传的规律,并由此为科学提供了大概是史上最有力的实验设计工具。对遗传的研究最终使得DNA的本质——基因在DNA上的结构和位置,以及蛋白编码方式等——得以发现。不过,孟德尔式的思维方式却让我们成了决定论的囚徒。对基因功能的阐释,让我们不光把其视作基因,而是联想到其所产生的性状。就如同是说豌豆种子中就包含着小小的绿色豌豆,或者受精卵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人一样:这是一种对基因功能的迷信。
孟德尔发现遗传就如同抛硬币一样是概率事件。父亲和母亲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基因的两个拷贝,他们各自随机地将其中一个拷贝遗传给后代。一旦某个拷贝随机遗传给后代,基因在其后代身上的作用遵循着决定论式的法则:结的豌豆不是绿色便是黄色,不是圆粒便是皱粒。
让基因看似起决定性作用的例子很多,孟德尔的豌豆就是一例。成百种已知的疾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一个或很少几个破坏基因功能的突变引起的。其中,包括囊胞性纤维症(Cystic fibrosis)、肌肉萎缩症(Muscular dystrophy),以及瑞特综合征(Rett syndrome)和黑蒙性痴呆(Tay-Sachs disease)这样的神经系统疾病。不过,这种“孟德尔式”的遗传病有一个规律——都是出现在生命早期的一些罕见性状,并且不受生活方式的影响。像这样的遗传研究在医疗领域的成功,只不过是摘下了那些“唾手可得的果实”,离大丰收尚有距离。
我们没少做尝试。花了数十亿的美元去寻找肥胖、心脏病、II型糖尿病、中风、高血压、癌症、哮喘和其他常见病的基因。但像样的成功倒是没有几个。而令人难堪的是,对于大多数疾病而言,患者的亲属患病的概率更高,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共同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基因对患病风险必有重大影响。而这更大大地巩固了DNA的象征地位。不过,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当我们试着去寻找的时候,它们又怎会从指间溜走呢?原因就在于,基因的决定作用不但取决于遗传与否的概率,也取决于其作用大小的概率。
我们在学校所学到的标准的“科学方法”,是对一个特定基因具有何种功能的假说先进行阐述,后进行实验。例如,有假说认为低密度脂肪酸(LDL)受体基因发生突变,可影响胆固醇水平,进而引发心脏病。然而,针对这一假说的大部分实验都无果而终。自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肇始以来,全基因测序技术的使用愈加广泛,使得这种以假说为基础的遗传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无假说”的遗传研究所取代。
与DNA的象征性一致,遗传学研究也假设某种目的性状肯定由基因引起,所以要从全基因组的角度,找到更常见于性状携带者身上的遗传变异。人们希望,待对基因水平的变异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便能很快消灭大多数人都会罹患的衰竭性或致死性疾病。
寻找决定性基因的遗传研究的规模已经变得更大、耗资也更多,但却欠缺重大的成果。遗传对某项性状或疾病的整体影响大部分还不清楚。相反,我们发现性状受多基因控制,就是说基因组中许多不同的部分都对个体有微小的影响。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就是一个研究颇多的典型例子。这是一种炎症性肠病,能够在家庭成员间散播,所以似乎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但是,最近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的一项研究估计,同某种特定疾病相关的基因大约有两百个,大部分基因的作用都很小,只能解释这种疾病遗传背景中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把这和抛硬币相比,基因变异同样以一种概率的方式对疾病风险产生影响,不过这种概率通常很小,远不到五五开。而且也不能保证同样的变异在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种群、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的携带者身上产生同样的疾病风险,就好像每枚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都在不断变化。因此,“个体化基因组医学”的预测效果很小,就如同试着要去预测几百个不一样的硬币抛起的结果一样。这就是为何除了少数的例外,遗传研究的临床或治疗价值迄今都微乎其微。
常见性状也和疾病如出一辙。身高是一种易于测量,且明显具备家族遗传性的性状。很多研究都试图寻找同身高有关的基因。光是有影响的基因区域就找到了400有余,而据估计,这个数字将超过700。但基因的作用依然微乎其微。《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至今只有一成有关身高的基因变异得到了解释。肯定会有更多与身高有关的基因被发现,而像饮食和疾病这样的因素也对身高产生着影响。
身高和克罗恩病只是冰山一角。而行为学性状和精神特质的预测也颇棘手。在酵母、昆虫和植物物种上进行的实验的结果也是如此。而这就是大自然的本来面目。无论那些还抱着基因决定论这样的简单论调的人有多不情愿,但复杂的性状是受多个功能微小易变的基因所影响(而非决定)。另外,有一点毫无争议,疾病风险通常都有一个强大的,且常常是决定性的环境因素。不过一般情况下,遗传学家都不太把这当回事。而这些环境因素本身,通常也很复杂,很难辨明和评估。
这些现象之下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当许多基因都可以影响一个性状的时候,或许每个人身上起作用的基因变异可能都不同。这是一个多对多的决定关系:有许多分子通路都影响着身高、血压、甘油三酯、胆固醇水平这样的指标。同样的,某个特定的基因型可能同许多性状有关。每一个基因变异都是一次作用微小,概率不定的“抛硬币”。每个人都在抛一组不同的硬币。所以,即使我们搞清楚了一个人的基因型,也不能很精确地预测其作用,就算“个性化基因组医学”宣称其作得到。
一个人的未来可以通过基因来预测吗?
这也让DNA的象征意义有了另一方面的疑问。与其将生命看作是达尔文学说中原始无情的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不如看作是一种合作。这里的合作不是说社会或感情因素,而是说一个性状由许多因素共同产生,数不清的基因和生活方式都作用于这一性状。如果这些因素没能充分协同配合,那么这一性状就不出现在胚胎中。我们身体中存在着许多相互作用的网络,像基因和基因之间、细胞器与细胞器之间、细胞与细胞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如此一来,除了很罕见的灾难性情况外,单个基因自己既做不了什么孽、也成不了什么事。即便通往失败的道路很多,哪怕是最罕见最严重的基因突变出现,也还有更多的道路通往成功。
演化所带来的冗余,能使个体免受有害突变的戕害和过于残酷的自然选择的淘汰,这也可以看作是基因间合作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基因本身并不是某些有用性状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生物体通常在这个基因变异或缺失的情况下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有其他基因能够填补空缺,或者基因变异本身的效果就微不足道。我们知道,许多臭名昭著的疾病的相关基因突变,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就是正常状态。全基因组测序不断地证明,就算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带有大量失活或严重异常的基因,其中可能包括那些明确地代表某些疾病的基因变异。
 或许因为我们是一种尚在演化的物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不安。这或许就是基因是生命因果关系中的决定因子这一想法这么易于接受,而其细节之处又如此容易被忽视的原因。Shutterstock 友情供图
或许因为我们是一种尚在演化的物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不安。这或许就是基因是生命因果关系中的决定因子这一想法这么易于接受,而其细节之处又如此容易被忽视的原因。Shutterstock 友情供图
所有这些可能令人迷惑:基因是一种是对生命起决定性作用的分子,然而它们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并且很难预测。我们已经试图去解释这种现象,尽管对于遗传和演化的研究通常技术性都很强,但研究的问题却很直白。我们很幸运,对生命和演化如何运作一点一滴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懂得在我们的本质当中究竟遗传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遗传这些东西。
借此,我们可以回归到自由意志这样有趣的行为学话题。我们现在知道,复杂的组织是由一系列决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就算单个基因不能算得为某项发育做过贡献,但就如人体、技能、骨骼、语言,甚至是足球队这样的复杂组织,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且有物质上的基础,而非什么神秘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实际上,这些“涌现”的复杂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在迥异的情境下,对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生理学和自由意志的同一种挑战。
不过,又回到我们早先提过的难题:如果科学说世界是一个遵从普遍的因果律的完全唯物的现象,那么就算是我们要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负责的说法,也要变得岌岌可危。人格?智力?犯罪行为?政治倾向?凡是能觉得出的,就算是我们的道德决断,也一定可以从我们内在的、遗传的基因组中得到预测。然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像糖尿病或者身高这样极端复杂的生理性状,它们更是远超以基因为基础的预测的能力所及。这是一种由于科学知识的暂时不足而导致的现象,亦或是其中还有什么更加影响深远的东西?
问题绝非偶然,因为这个问题源自心身二元论的惯性思维。二元论认为,无论思维和意识是什么,都不受物质约束。换句话说,从自觉拥有自由意志起,我们便拥有自由意志。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道义上的责任,而这一假设的核心便是自由意志。这样的假设又影响到社会和法律政策和获得救赎的宗教观念。显然,如果人只是其基因的产物,那人何须担当责任。然而,人又怎会不是基因的产物呢?
通过了解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复杂的因果关系,或许能找到答案。我们还不够资格谈道德责任这样的信仰问题。不过从科学的观点看,心身二元论是不存在的。思维尽管很奇妙,但事实上也是包括基因等分子的产物。然而,思维似乎根本无法基于基因而预测。原因在于大脑和其活动是数以十亿、百亿,甚或更多的分子和细胞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基因的活动与否,到神经连接的形成,每一次作用都存在着概率。这样的相互作用从我们出生之前便开始,跨越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在发育过程中,我们的大脑神经间形成连接的方式都差不多,不过对于每个人而言,神经连接的形成则是出于其个人经历的结果。个人的行为就是大脑对我们独特经历产生反应的结果。
我们一点也不必惊讶。行为就和其他性状一样,也不能通过基因明确地预测出来。由可能性交织成的巨大网络,使行为预测的效果和预测性状一样微乎其微。我们的精神活动似乎是自由的,其不可预测性加强了这种感觉。然而,这种感觉的原因在于精神活动中包含的因果关系太过复杂。实际上,到底有多少相关因素参与其中都尚不可预测。从这层意义说,实际上我们确实是自由的。
有一点要指出。所有这些关于决定论、概率和复杂因果,甚至是它们对自由意志影响的问题,都并不新鲜。这些问题能够追溯至古典哲学时期。在18到19世纪,随着概率和统计的发展,这些问题亦经历激辩。待到20世纪的亚原子物理大发现时,讨论亦愈加热烈。人们也认识到了多因子概率因果分析的重要性和挑战。而从基因的角度,又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不过从概念上讲,我们对宇宙(其中包括生命)运作方式的理解,并没有多大进步。
人类不喜欢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可预测性为我们带来了想要的安全感。或许因为我们是一种尚在演化的物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不安。况且,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觉得因果关系该有个唯物的理解。这是一种简单且易于理解的决定论式的想法。我们想要手握大权,想要掌控自然,以便让我们这些终将灭亡的生命,在这个终将灭亡世界上,能够少面对些难题。我们希望生命里真正的因果关系能够直白些。所以,这或许就是基因是生命的因果关系中的决定因子这一想法这么易于接受,而其细节之处又如此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我们生来不太能接受悬而未决的事情,除非如抛硬币这样,我们其实能觉察到结果的事情。当有一件无法预见的事,其中又蕴含多对多的因果关系时,事情就远非我们的思维可以处理了。然而现实世界似乎恰好如此。
相关的果壳网小组
编译自: Aeon 网站,Things gene can't do
文章图片:Shutterstock 友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