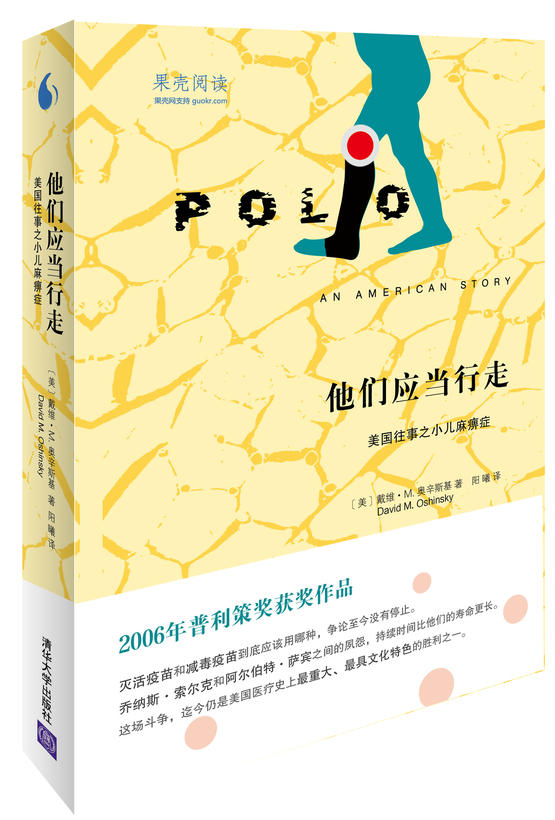背景阅读: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母亲在行动
(妲拉/译)
1947年,自人类首次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脊髓灰质炎仍是科学界的未解之谜,而且解决它的希望似乎日渐渺茫。1910年,人们觉得安全有效的疫苗几个月后就能问世。但在那以后,科学界遭遇了重重障碍,很多研究者甚至开始怀疑到底能不能找到有效的疫苗。
哈里•韦弗的疫苗计划
面对这样的局面,巴塞尔•奥康纳在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里设立了一个新职位:科研督导,坚韧的哈里•韦弗(Harry Weaver)坐上了这个位置。韦弗面对的是一场硬仗。有的人认为压根就不应该设置这个职位,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督导”;而有的人则警告他最好小心行事——我们是按照不同方向开展研究的独立个体,不是马戏团里听口令表演杂耍的海豹。

哈里•韦弗是脊髓灰质炎圣战中的无名英雄之一。1946年至1953年期间,他担任国家基金会的科研督导,他革新了资助科研、管理资金和持续资助的方式,加快了美国脊髓灰质炎研究的步伐。
对韦弗来说,解决脊髓灰质炎的唯一方案就是成功研制出疫苗。我们显然无法将脊髓灰质炎从周围的环境中彻底清除,也无法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检疫隔离。谁也没法阻止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人体,而一旦它侵入人体,也没有任何药物或者化学物可以抵御它的进攻。新出现的抗生素对细菌感染疗效极佳,却似乎无法对抗病毒。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疫苗刺激免疫系统,在这种致残病毒发起进攻之前产生足以抵御它的抗体。
疫苗已经成功征服了其他病毒,例如天花和狂犬病。如果疫苗能有效地赋予人类对脊髓灰质炎的抵抗力,那很可能这种疾病就会寿终正寝,因为人类似乎是它唯一的天然宿主。
韦弗认为,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搞出疫苗,显然是因为研究界缺乏合作。多年来,基金会的受益人各自为战,还常常互相保密。疫苗采用活病毒还是灭活病毒,对韦弗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实际上基金会情愿同时资助两个方向的研究。重要的是扫除多年来阻碍脊髓灰质炎疫苗问世的障碍。
疫苗计划还能让韦弗有机会招募一批新的人才——不墨守成规、没有任何偏见和预设观点的年轻研究者,他们会和他一样感受到问题的紧迫性。在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身上,他找到了自己正在寻求的东西。索尔克生于1914年,毕业于纽约大学医学院,师从病毒学先驱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此时,他刚刚离开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离开弗朗西斯,来到当时并不入流的匹兹堡大学,领导那里新成立的病毒研究项目。
病毒到底有几类
要制造出有效的疫苗,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首先,必须确定脊髓灰质炎病毒到底有几种。其次,必须为每种类型的病毒找到安全稳定的供应源,以用于疫苗生产。第三,必须搞清脊髓灰质炎真正的发病机制——它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路线,以确定疫苗起效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实际上,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科学家。韦弗就任科研督导几个月内,就启动了基金会历史上最具野心的项目:归类全世界所有已知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有的病毒非常稳定,例如天花;而有的病毒十分多变,例如流感,流感疫苗几乎每年都需要更新换代。脊髓灰质炎属于哪种?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路只有一条:动手归类。归类病毒的工作十分枯燥无趣,弗朗西斯和萨宾(Albert Sabin)这样的大牌通常会把这种活儿交给技师或是研究生去干。这不是通往诺贝尔奖的捷径。韦弗也说:“整个医学研究领域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趣的事情。要得出最后的结果,必须无数次机械式地重复一套完全相同的技术流程,测试一个又一个病毒,每周7天,每年52周,整整3年。”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干这活儿?韦弗前往匹兹堡拜访索尔克,十分慷慨地抛出了他的条件:索尔克会连续数年拿到基金会的一大笔资助。虽然索尔克最有兴趣的病毒不是脊髓灰质炎而是流感,但现在的时机恰到好处,索尔克已经抢到了先机。1948年,他收到了基金会的第一张支票,金额是41000美元。从1949年到1953年,他从基金会获得了近百万美元的资助。
在国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乔纳斯•索尔克在匹兹堡大学的一所医院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索尔克的实验室完成了大量测试工作。利用脊髓灰质炎患者及其家人的粪便、喉部培养样品和死亡患者的神经组织,他们仔细检查了数十种病毒株。索尔克收到的很多样本来自基金会的其他受益人。每份样品都附有简单的说明,例如,“明尼苏达病毒源自依斯琳•蔡斯太太尸体解剖获得的组织,解剖日期:1946年7月24日。疫情发生时患者居于明尼阿波利斯,延髓型脊髓灰质炎发作三日后死亡……样品以玻璃安瓿封装,干冰冷藏。”
归类项目从1949年进行到了1951年。基金会的总花费超过12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和照顾实验用的猴子。猴子对脊髓灰质炎研究非常重要,它是科学家研究这种疾病最常用的实验动物。但猴子的价钱很贵,也很难搞到。
光是病毒归类项目就牺牲了17000只猴子。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将脊髓灰质炎人类患者的粪便样品注入猴子脑部,然后每天让猴子运动,观察有无明显的脊髓灰质炎症状。一旦出现瘫痪,就将猴子杀死,取出大脑和脊髓获取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将含有病毒的组织-血清混合物注入健康的猴子脑部。科学家认为,已经接受过I型病毒注射并顺利康复的猴子应该对其他所有I型病毒免疫。“然后,将未知类型的病毒注射给猴子,如果它很容易被感染,那就意味着这种未知病毒应该属于II型或III型……接下来再重复这个过程,用同样的未知类型病毒来测试已经对II型或III型病毒免疫的猴子。”
毫无疑问,归类项目让索尔克与基金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但它同样标志着索尔克在论资排辈的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地位低下。在一次会议上,他就程序问题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觉得自己的态度相当谦逊。“阿尔伯特•萨宾……转身冲着我说:‘索尔克博士,以你的学识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啊。’”索尔克回忆说,“那简直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索尔克忍气吞声,前往辛辛那提拜访萨宾的实验室,说了些恰到好处的恭维话,甚至还在萨宾家里过了一夜。他不吝溢美之词地感谢萨宾送来的论文副本和待分类的新病毒。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萨宾不太看得起索尔克,这一点从未改变。他觉得索尔克不过是国家基金会手下一个跑腿的,野心勃勃但是资质平庸,为了出人头地对哈里•韦弗俯首帖耳。
归类项目的最终结果十分让人安心,接受测试的196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可以完美地归为三种不同的类别,脊髓灰质炎病毒“家族”非常小,这真是件幸事。
I型病毒涵盖了82%的病毒株,II型占10%,III型占8%。研究者给每个类型的病毒起了个绰号,I型病毒叫“布伦希尔德”,这是博迪恩实验室里一只黑猩猩的名字;II型病毒叫“兰辛”,以纪念密歇根州兰辛市的一位已故患者;III型病毒叫“里昂”,与它同名的洛杉矶小男孩也死于脊髓灰质炎。
在体外养出病毒
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成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必须为全部三种病毒提供免疫力。研究界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没有成功培养出可用于疫苗生产的足够多、足够安全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此前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1907年,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罗斯•哈里森(Ross Harrison)作出了一个发现,有人盛赞为“西方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发现之一”。那就是组织培养的概念:在宿主(植物、动物或人类)体外培育活细胞的能力。两位声誉卓著的研究者写道:“哈里森的发现让我们得以在细胞层面甚至分子层面上研究活生生的有机体,从而促进了现代疫苗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组织培养,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对疾病基本机制的了解比过去五千年都多。”
1936年,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萨宾和彼得•奥利茨基(Peter Olitsky)证明了我们的确能在试管里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不过,它只在神经组织中生长。
这个结果是有原因的,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里普遍采用的是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的“MV”病毒,这是一种高度嗜神经性的病毒株,只能在神经组织里生长。
于是研究者陷入了窘境,因为如果把猴子的神经组织注入人体,就会引发脑脊髓炎。如果萨宾和奥利茨基是对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只能在危险的神经组织里生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集病毒来制造疫苗?
事情到这儿就卡住了。同时挑战西蒙•弗莱克斯纳和美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所里两位灯塔式人物的智慧,这并非易事,每一位病毒学家都相信他们——可能只有哈佛的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是个例外。
今天,约翰•恩德斯是医学史上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他还不怎么出名,这已经是最客气的说法了。恩德斯生于康涅狄格州,短暂地从事过地产业,还上过英国文学的研究生,最后拿到了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后,他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病毒性疾病研究。
1947年,恩德斯开始担任波士顿儿童医院传染病实验室主任,他的一小部分资金来自国家基金会给哈佛的20万美元研究经费,这时候国家基金会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存在。实验室的第一批成员里有两位有志于病毒性疾病研究的儿科住院医生,弗雷德•罗宾斯和汤姆•韦勒。此时体外培养技术正在迅猛发展。青霉素和链霉素之类的抗生素投入使用,有效地防止了细菌污染,培养基更容易保持无菌环境。实验室采用了新技术缓慢地滚动试管,使得试管内的组织能够接触适量的液体和空气。汤姆•韦勒发现,如果定期更换营养培养基,组织会存活更长时间。

1948年,约翰•恩德斯(左)、托马斯•韦勒(右)和弗雷德里克•罗宾斯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能在试管里的非神经性动物组织中生长,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安全、充足的病毒来源。因为这一贡献,他们三人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奖,成为仅有的获此殊荣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
恩德斯实验室的大突破主要来自科学直觉。“有一天,汤姆和我正在准备一套新的培养基,”弗雷德•罗宾斯说,“恩德斯博士建议说,实验室冰箱里存了一些脊髓灰质炎病毒,不如试着培养一下。”培养基里既有神经性的胚胎组织,也有非神经性的。四份注入了水痘病毒,四份注入兰辛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还有四份是空白对照组。
韦勒和罗宾斯对实验结果没什么信心,但恩德斯有一种直觉。他回忆道:“我一直觉得,既然我们在消化道里找到了这么多脊髓灰质炎病毒,那它一定能在神经组织以外的地方生长。”
他的本能是对的。兰辛病毒株不光在神经组织中生长,还在皮肤、肌肉和肾组织中成功繁殖。接下来几个月里,针对I型和I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组织培养同样获得了成功。科学界花了整整40年,无数次走进死胡同,终于解决了脊髓灰质炎领域最大的谜题之一。
现在研究者可以在试管里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而不是猴子的脑子或脊髓里,于是他们能够更好地观察被脊髓灰质炎感染的细胞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安全地培养出足够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不再需要担心动物神经组织带来的污染,批量生产疫苗因此而有了可能。
恩德斯相当冷静。事实上,脊髓灰质炎从来就不是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他更钟情于其他病毒,尤其是麻疹,后来他还发明了广受欢迎的麻疹疫苗。但是,脊髓灰质炎让低调的恩德斯一举成名,1953年,他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次年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斯德哥尔摩发来官方通知时,恩德斯明确表示,除非让两位年轻同事罗宾斯和韦勒并列为获奖人,否则他不会接受这个奖项。他的慷慨行为成了科学界的标杆,未来大家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其他研究者,很多人都没这么大方,尤其是乔纳斯•索尔克。
病毒是怎么进入人体的?
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面临的两大障碍已经被清除,而在人体测试开始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有效性仍有争议。一代人的研究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鼻腔进入人体,然后绕开血液系统,直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刺激血液产生抗体、赋予身体天然免疫力的疫苗似乎没什么用处。
这套观念要追溯到西蒙•弗莱克斯纳的早期研究,他提出的各种脊髓灰质炎理论根深蒂固,多年来一直统治着整个研究领域。到20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对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已不抱希望,他鼓励奥利茨基着手研究“化学阻断”。
1936年,萨宾和奥利茨基恪尽职守地在猴子身上做了“鼻腔阻断”实验。与此同时,亚拉巴马州的公共卫生官员用苦味酸(一种有毒的酸)溶液和明矾在志愿者身上做人体实验。让人失望的实验结果促使科学界采用了更强效的化学物。第二年,多伦多疫情爆发期间,他们给孩子喷了硫酸锌。结果证明这种化学物无助于遏止脊髓灰质炎流行,反而导致了几个孩子“显著而彻底的永久性嗅觉丧失。”这场闹剧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化学阻断”的惨败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脊髓灰质炎到底是如何进入人体的。
萨宾冲在最前线。在1941年的一次突破性实验中,他采集人体解剖材料,证明了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消化道里有大量病毒,但鼻腔里却很稀少。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者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们切除了一只黑猩猩的嗅觉神经,然后给它口腔饲喂了大剂量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正如他们所料,黑猩猩很快被病魔击倒了,这同样证明了脊髓灰质炎不是通过鼻腔传播的。
弗莱克斯纳的理论被推翻了。如果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口腔进入人体并沿着消化道下行,那它在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必然会经过血液,那么设计用于提高血液中抗体水平的疫苗应该能在病毒造成严重后果之前把它干掉。
耶鲁大学的多萝西•霍斯特曼(Dorothy Horstmann)是第一批将目光投向这个方向的研究者之一。“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间很早,1943年纽黑文疫情爆发期间,我采集了医院里每一位病人的血样。我记得很清楚,一共测试了111份血样,其中只有一份检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个概率可不算高,所以我们觉得病毒进入血液也许不是很常见的事情。”

备受同行尊敬的多萝西•霍斯特曼是脊髓灰质炎研究先驱之一,也是耶鲁医学院首位女教授。
不过,霍斯特曼对那唯一一位血液中检出病毒的患者很感兴趣。那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如果不是疫情爆发,医院大概永远不会发现她得了脊髓灰质炎”。除了轻微的颈部疼痛以外,小女孩没有表现出其他任何脊髓灰质炎的症状。霍斯特曼开始怀疑,会不会是这样:只有在患者表现出明显身体症状之前的一小段时间,脊髓灰质炎病毒才会出现在血液中?
为了验证这套理论,霍斯特曼开始在黑猩猩身上做一系列实验。她通过口腔给它们饲喂脊髓灰质炎病毒(“天然的感染途径”),目的是确定病毒是否会出现在血液中,如果会出现,那具体是什么时间。结果相当惊人。饲喂几天内,血液中就检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是怎么回事?以前的研究者为什么没发现血液里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答案简单得要命:他们等了太长时间才开始检测。
一旦脊髓灰质炎进入血液,就会产生将它摧毁的抗体。所以,只有在抗体形成之前那个短暂的酝酿期内,你才能在血液里检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少数情况下,病毒会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瘫痪甚至死亡。但哪怕它进入了神经系统,血液里也不再有病毒的踪迹,因为血液中产生的抗体已经将它彻底扫除。
这个谜题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了解答。研究人员找到了免疫系统对抗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时机(感染早期)和战场(血液中)。
我们将通过疫苗征服脊髓灰质炎。(编辑:od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