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9月14日~20日,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又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前不久,我撰写了“解码科学传播”系列专栏文章的第一篇《中国科学传播做对了什么》。文中简单提了下中美科学传播的主要区分。现在借着观察全国科普日的活动,我将对两种科学传播体系进行对比,详细讲讲两者间的区别。
 2019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 | 人民网
2019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 | 人民网
实际上,我对中美之间科学传播体系差异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刚开始到美国启动系统的科学传播学术训练与研究时,怀着一种膜拜的心情,但随着了解的加深,发现很多对美国科学传播能力的理想化想像不断被现实所消解。但是当我临近回国,开始强化科学传播实践方面的训练时,又发现了中美之间新的差距。
 中美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 | pixabay
中美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 | pixabay
然而,本文并非要在中美科学传播之间比出一个优劣短长,而是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与科学活动的其他门类一样,不同国家之间科学传播的形态与模式的差异,更多是彼此迥异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简单地厚此薄彼,并不能让我们真正通过借鉴各国经验,在自己的科学传播事业上取得实质性进步。
冲在科学传播前沿的大学
到美国之前,经常通过媒体和各种科学传播研讨活动,感受国外科学传播风风火火的局面。然而在美国若干所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普渡大学、迈阿密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学习、观察数年后,既感到收获多多,也体会到想像与现实的差距。
 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名校 | harvard.edu
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名校 | harvard.edu
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各个高校都非常重视科学传播。每所学校的传播团队,都不少于几十人,而且基本上每个院系,都会有负责传播职能的职员。总体来讲,公立大学校级传播团队较大,管理更加集中,而像哈佛和麻省理工这样的传统私校,每个学院都有自己很强的传播团队。当然,传播团队并不都是从事科学传播,但美国大学对外发布的新闻,科研成果占了压倒性的比例,所以其中科学传播的专职写手和组织人员数量想必不少。
即便以如此大的科学传播团队,各校也鲜见有类似于中国的全国科普日或科技周这样的统一科普活动,基本上都是每个院系各搞各的。8年来,我没有看到任何学校安排的校级统一科普行动。所有院系以上级别的科学传播行动,几乎都依赖于这些大学所在地公民社会的推动,尤其是当地科技馆等科普社团组织倡议的结果(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科学节)。
不用问,这种差异源于中美科学传播管理机制的不同。中国有着以中国科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科普动员系统和科学传播组织体系,美国既没有全国性的科普主管部门,在学校层面也没有自上而下的传播管理体系,我所见的大多数美国大学的院系传播部门与校级传播部门彼此完全独立,互不隶属。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并不能充分揭示中美科学传播机制的不同,我们在对比了中外科学传播的其他方面后,在本节的末尾再来深入分析这一点。
科学家做科普并非尽善尽美
除了上面的赞叹,其实失望也不少。比如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基本不会参与常规的科普活动,甚至有不少美国科学家抵制热衷于参与公众传播活动的同行,认为后者有借助公共影响力获取科研资源的嫌疑。记得几年前拜访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现任南方医科大学校长的黎孟枫教授,他提到其在美国任教时,很多同事对积极参与科学传播或直接与媒体打交道心存顾虑。
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如此,院士都会抱怨因为参与科普而被同行另眼相看。比如一位网红科学家告诉我,他曾经给一位热衷科普的院士当秘书,而这位院士因为积极向公众进行科普活动,经常被一些同行排斥。
科学传播课程开设情况,美国当然比中国普遍很多,但我统计过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开设的科学传播课程及培训班,每年能覆盖到的科学家或博士生、博后数量也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即便算上累积效果,接受过科学传播培训的人也远远达不到十分之一的科研工作者。
的确,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常规性参与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总是少数,科普也很难被视为让科学家全力拥护的行为。前不久还听朋友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科研成果进行强制性公众教育(Public Outreach)的要求,实际上也在美国科学家中引发了反弹,一些大腕科学家甚至因此不去申请NSF的课题,转而申请没有科普义务的私人基金会经费。我当时正在兴冲冲地规划如何推动中国科研基金施加强制的科普规定,这个消息无疑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网 | nsf.gov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网 | nsf.gov
尽管美国科学家没有想象中那样热衷科普,但科学界对科学传播的推动却当仁不让。除了上面提及的大学对科学传播的大力支持和NSF强制要求大多数科研项目进行公众教育外,美国科学界对科学传播的能力建设也非常上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培训能覆盖到每位科学家。
以201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为例,年会上有关科学传播的各种类型的培训活动,足有几十场之多。这些以研修班为主的活动涵盖了科学媒体关系、公众沟通技巧、互联网科普操作指南和社交媒体利用等科学传播的基本手段,也囊括了实验室摄影摄像、网络视频利用、漫画书写科学以及科学戏剧展示等各种热门科普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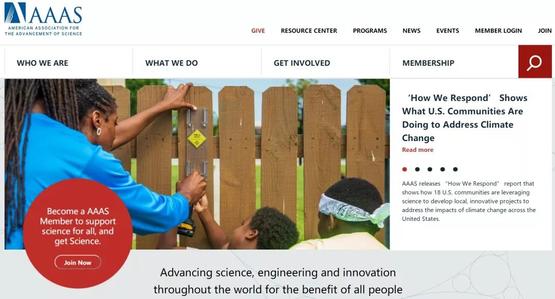 美国科学促进会官网 | aaas.org
美国科学促进会官网 | aaas.org
除了科促会等大型综合科学会议外,美国很多自然科学的学术年会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科学传播技能培训内容。而且培训之外的服务举措也很多。科促会、美国化学会、美国地质学联盟等机构都提供了对会员的免费科学传播服务。而在大学中,各种科普社团更是数量繁多,与中国的科普组织重在内容呈现不同,很多美国的科普社团重在提供平台、专业化服务和社会与科学界之间的联系。比如一个扎根在多所大学中的名为“草蜢”的组织,专门组织大学生为大学所在社区或临近的高中作志愿者,讲授科学方面内容。在康奈尔,我还参与了一个名为拓展科学训练(Broadening Experiences in Scientific Training,BEST)的项目,由NSF资助、依托几十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开展博士生、博士后的传播、就业、创业等学术相关能力的训练。
科普行为背后的文化与制度差异
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中美在科学传播上的管理与组织体制的差别外,又有些什么其他因素造成了两者的差异呢?在探讨差异前,不妨先看看共性。
就共性而言,如我在《中国科学传播做对了什么》的分析,中国、美国或者欧洲,都在政治上升华了科学传播的意义,让科学传播成为了高度政治正确的事业。但无论中外,科学传播本身,都没有成为科学家的必备行为。在一般意义上,科普行为也没有成为科学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的确,更多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会让科学获得更多社会支持,但这与很多公益行为一样,对科学家个体缺乏约束。虽然大量研究表明,吸引媒体的关注会让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同行关注和引用,但毕竟绝大多数科学工作是不会被媒体报道的。一项研究曾估计,每年全世界以英文发表的数十万篇科研论文,能被媒体报道的数量至多不过百分之一。
所以,看起来大部分科学家不参与常规科普工作,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一件正常合理的事情。而科学传播的制度安排,并不是让每一个科学家都要从事科普,而应该是通过提供科学传播资源、平台和路径,激励科学家从事科普,从而达到如下三条核心的目标:第一,创造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民科学素养提升的科普供给;第二,让各种科学机构可以通过向社会供给科普而满足特定机构需求;第三,让有潜力有意愿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共同体成员能获得渠道、资源与支持。
按照第一点目标,中美之间在科学传播上的差异不在于各自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科普供给,而在于这种供给呈现的方式,一如中国社会的其他服务都要服从于集中管理一样,中国的科普供给也自然符合从上而下统一安排的节奏,通过行政手段来调动机构和个人的参与。而欧美科学界即便需要国家财力支持,但在制度安排上各大学都是独立的,院系与学校的关系虽有从属,但从属的往往是协议约定的人财物等关键事项,科普则不在这一体制中。所以科学传播上的自行其是也是题中之意。
 为了争取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人们走上华盛顿的街头进行游行 | unsplash
为了争取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人们走上华盛顿的街头进行游行 | unsplash
中美科学传播体制在第二个目标上的差异,则涉及到科研机构自身面临的激励和约束因素。从激励而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最大的收入来源往往是社会捐赠和学费这两块,它们都与学校树立积极的科研形象密不可分,自然这也是推动大学成为科学传播主力的主要原因。相对于科学群体而言,捐助人绝大多数就是社会公众的一部分,这也促使美国大学提供的科学报道紧密围绕着公众需求。
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当然也有宣传自己科学成就的动力。但由于中国的科研资源来自于行政体系的拨款,所以报道科学的第一动力是汇报工作及其成果。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大学发布的科学报道新闻稿更像是科研机构的行为与成绩总结,其中,科研成果的价值也往往被等同于科学知识自身的意义或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支持。
从条件约束的角度,中美最根本的区别则是两国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可以动员的资源的巨大差距。美国大学接受的捐款,大量可以用于软性的人力资源开支,而科研课题的校方管理费提成(overheads)比例远高于中国,这就导致它们可以在科学传播这种服务上保持一定开支甚至购买服务。而中国即便现在有了很多面向教育的捐助,其目标也主要是盖大楼和向学生提供奖学金。至于行政拨款,在严控事业编人头的原则下,大学宣传部或中科院各院所的综合办公室本来就没几个人,还要承担大量党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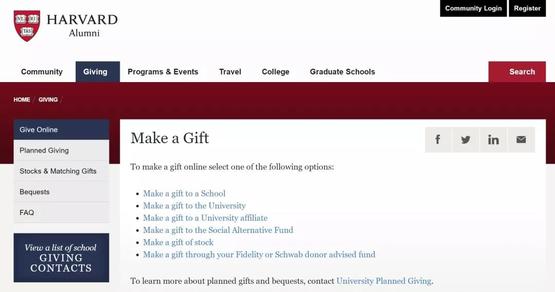 哈佛大学官网的捐赠页面 | harvard.edu
哈佛大学官网的捐赠页面 | harvard.edu
上述激励和约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高举科普重要性这杆大旗的同时,能实际投入的资源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投入相关资源,产出的结果也往往是有关科研活动的表功笔法。
在落实第三个目标,即为科学共同体个体成员提供科普支持方面,应该说中美两国都很重视。但如上所述,美国通过研究生课程、在校培训、专业学会和行业公共事件(如科促会年会或美国化学会年会),已经提供了大量相关支持(虽然这些支持的目的不是达到全员科普),而中国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能够覆盖到个体科学家的培训还相当有限。除了上面分析的体制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科学传播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各级科协系统及所属学会是专业科普的主力,但科协系统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约束力有限、实际渗透仍然不足,很难调动个体的科学家。
探索科学传播的未来方向
回到本文上面探讨的中美在科学传播组织和动员上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在目前国情下,具有行政动员色彩的科技周或科普日等统一活动对于推动科学传播,仍然很有价值。虽然这些活动由于自上而下的安排,对于真正激发科学共同体投身科普实践缺乏持久性效果,但行政性的动员,恰恰是目前情况下对科学传播最有力的执行工具,也最有可能相对弥补体制因素造成的对科学传播的激励不足(如何激励科学传播,我将在后续的专栏文章中结合对科学传播正高职称一事进行评价)。
上述内容通过对比中美在科学传播上的表现、管理与机制的差异,揭示了很多短期难以扭转的制度化因素对中国科学传播的影响。但揭示出这些不尽人意的制度化因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我批评,而是为了在理解“复杂中国”的前提下设计出可行的政策解决方案。
诚然,这篇小文难以承担提供解决方案的重任,但我们完全可以在难以撼动根本体制性因素的前提下,通过试点探索,创造微观激励,以及根据个案实施效果做局部调整等手段对中国的科学传播做出推动。这也是我们对比中美科学传播体制的价值所在。(编辑:Yuki)
